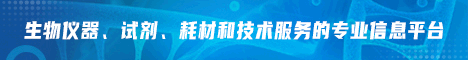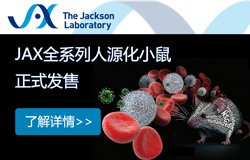最新精準醫療蛋白質組里程碑事件的思考與研究成果解讀
最新精準醫療蛋白質組里程碑事件背后,我們還看到了什么?
無論是關注蛋白質組學的領域內專業人員,還是領域外、甚至是學術圈外的,我想很多人此刻都難掩興奮。2019年2月28日,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國家蛋白質科學中心(北京)、蛋白質組學國家重點實驗室賀福初院士團隊、錢小紅教授團隊,與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樊嘉院士團隊,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Nature》上以《Proteomics identifies therapeutic targets of early-stag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為題,在線發表了早期肝細胞癌的蛋白質組研究的重磅成果。該研究國際上首次描繪了早期肝細胞癌的蛋白質組表達譜和磷酸化蛋白質組圖譜,并進一步發現了重要的肝癌精準治療新靶點。該研究之所以刷爆朋友圈,不僅是因為其完全來自于國內研究人員,再次證明我國的蛋白質組學研究在國際上的頂尖定位;更重要的是,該研究注定將成為蛋白質組學應用于精準醫療的里程碑。

Proteomics identifies therapeutic targets of early-stag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原文鏈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9-0987-8

科研人員討論質譜數據,前排右為賀福初院士,左為錢小紅研究員。(洪楠攝影 軍科院供圖,來源于央視網 侵刪)
我們先回顧一下該研究的內容與成果:
該研究收集并選擇了101例早期肝細胞癌患者癌癥組織及配對癌旁組織樣本。利用基于質譜的蛋白質組與磷酸化蛋白組技術,對上述樣本進行了系統性地蛋白質、蛋白質磷酸化修飾的定性與定量分析,國際上首次描繪了早期肝細胞癌的蛋白質組表達譜和磷酸化蛋白質組圖。

以此為基礎,該研究將將目前臨床上認為的早期肝癌患者,更精細地分成了三種亞型S-I型、S-II型和S-III型,與臨床數據的相關分析表明,該分型具有明確的臨床意義: S-I亞型的癌患者僅需手術,要關注過度治療;S-II亞型的患者不僅需要手術,還需要聯合輔助藥物治療;而S-III亞型則預后最差,術后發生復發轉移的風險最高。

如果僅僅是繪制早期肝癌圖譜及提供相應的臨床分型基礎,該研究不足以登上頂級期刊,對臨床治療的意義也會相對有限。進一步通過對組學數據進行挖掘,研究人員進一步揭示了在信號通路水平上的特征性變化,并在此基礎上找到了一個關鍵的潛在治療靶點——甾醇O-酰基轉移酶(Sterol O-Acyltransferase 1,SOAT1),其異常表達水平與預后的相關性極高。

為了揭示該分子可能是重要的腫瘤藥物開發靶點,研究團隊利用肝癌患者的人源腫瘤異種移植(PDX)模型,證明了SOAT1的抑制劑阿伐麥布(avasimibe)在肝癌患者的人源腫瘤異種移植(PDX)模型上表現出良好的抗腫瘤效果,表明阿伐麥布有望成為S-III亞型患者的有效治療方案。在分子機制水平,該研究進一步證實SOAT1基因表達與細胞的膽固醇的攝入密切相關,進而通過影響分子整合素家族的豐度,參與腫瘤細胞的增殖和遷移。更有廣泛意義的是,團隊還發現SOAT1的蛋白質表達水平在多種腫瘤中(甲狀腺癌、頭頸癌、胃癌、腎癌和前列腺癌)均與較差的預后密切顯著相關。說明膽固醇代謝失穩與SOAT1的促癌機制很可能是多類腫瘤中共有的機制和潛在治療靶點。

在上述的研究數據與結論、以及其重要的臨床意義下,該研究的背后也許還存在著更多的意義和價值:
1. 腫瘤是基因病嗎?
這是一個學術結論相對明確,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也許又不完全明確的定義。以2001年人類基因組草圖的繪制完成為起點。多年以來,在腫瘤的相關領域內,無論是科學研究、臨床診斷、臨床治療領域,亦或是如火如荼的生物產業領域,基因、轉錄水平的檢測是最火爆、最必不可少的切入點和工具。相比于全民知曉的人類基因組計劃,即使是學術圈的科研人員,知道2014年人類蛋白質組草圖繪制完成的也是寥寥無幾。然而,隨著人類蛋白質組草圖的繪制完成,基因檢測一家獨大的局面發生了變化。從2014年到2018年陸續在《Nature》《Cell》正刊及其子刊發表了多篇重磅成果,已經完成的精準分型組學研究包括:子宮內膜癌、結直腸癌、乳腺癌、卵巢癌和胃癌等。

上述研究模式是將基因組、轉錄組、蛋白組及翻譯后修飾組的大數據整合起來,從多分子層面的大數據重新定義疾病的分型、挖掘潛在的治療靶點,最終在蛋白水平上發現與驗證腫瘤相關基因突變、表達變化及關鍵分子調控機制,以進行更精準的用藥指導和藥物開發,即所謂的“Proteogenomics”。幸運的是,該模式不僅停留在研究階段:在2016年美國癌癥登月計劃(Cancer Moonshot 2020)落地的同年,美國VA、DoD、NCI三部門聯合宣布將建立第一個同時進行基因信息和蛋白信息表征的醫學系統,把基因組和蛋白質組作為常規檢測手段,對癌癥病人進行個性化蛋白基因組(Proteogenomics)表征,為更精準的用藥提供指導,即“阿波羅計劃”(APOLLO)。“阿波羅計劃”正式將Proteogenomics作為核心理念和工作方式。

然而,雖然蛋白質組被越來越多地重視,但實際情況是:蛋白質組的研究仍然需要“背靠”基因組、轉錄組。蛋白質組學的數據一定要跟基因、轉錄進行比對,且更多關注于兩者數據的一致性,即蛋白質組進行精準醫療的研究一直以“Proteogenomics”的形象出現,而不是 “Proteomics”獨當一面。2018年,同樣來自上述研究團隊的秦鈞教授,在Nature子刊《Nature Communications》上發表的《A proteomic landscape of diffuse-type gastric cancer》的研究,發起了“Proteomics”獨自走上前臺的第一槍,該研究不僅為彌散性胃癌的精準分型提供了依據,其中發現的蛋白水平與基因水平數據的表達“異常”情況,也非常有啟發意義。

本研究中,雖然也分析了基因、轉錄水平的數據,但從文章名稱就可以直接看出,不再是《Proteogenomics…..》而是《Proteomics……》,是蛋白質組真正獨抗大旗。我想這不僅對眾多蛋白質組學人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對于腫瘤的研究、精準診斷、精準治療的未來發展方向也將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啟示。從最根本的生物層面不難理解:DNA、RNA并不是功能分子,而蛋白質才是,蛋白質是絕大多數的腫瘤藥物的治療靶點,以及最重要的臨床診斷指標。目前無數的研究數據告訴我們,無論是腫瘤領域還是其他醫學領域,抑或是植物學領域等等,轉錄組與蛋白質組數據的整體相關性是不高的。雖然從技術角度來說,與測序等技術相比,蛋白質組水平的分析技術還存在很多瓶頸,但從最終的生物意義和臨床意義為出發點,蛋白質分子必然應該成為主導。
2. 還是那句話,腫瘤是基因病嗎?
我們再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探討該問題。該研究的重要性,除了指導早期肝癌的精準分型,還在于其發現了一個促癌機制和潛在治療靶點——膽固醇代謝失穩與SOAT1。這就延申到了另外一個重要的分子層面——腫瘤代謝。腫瘤是一種代謝疾病,我想這個定義很多研究者都不會反對。腫瘤代謝是腫瘤領域最熱點、最有活力的方向。而近年來,國外的研究者已經意識到,代謝層面也可能幫助我們指導腫瘤的精準分型。這兩年,已經看到不少頂級雜志的高水平研究揭示了代謝分子與腫瘤分型與預后的關系。例如,《Cell Metabolism》上的一項研究通過蛋白質組學、代謝組學等實驗,揭示了HGSOC的代謝異質性,也闡明了慢性氧化應激與早幼粒細胞白血病蛋白過氧化物酶體增殖激活受體共激活子1α (PML-PGC-1α)軸之間的聯系(對卵巢的化學敏感性有顯著影響)。(Cell Metabolism:揭開“沉默的殺手”面紗,代謝組學+蛋白質組學進行高級別漿液性卵巢癌分型)以及,《Cancer Cell》的一篇研究曾經對138例腎透明細胞癌(ccRCC)患者的癌組織與正常組織進行了代謝組學分析,并通過與TGCA數據庫中的轉錄組數據以及臨床信息進行聯合分析,對ccRCC在代謝層面上進行了分子分型。(Cancer Cell:代謝組學如何玩轉大隊列臨床樣品)
然而,雖然代謝與腫瘤的關系已經研究得如火如荼了,但是大部分研究更多關注的是極性代謝物(如氨基酸、糖代謝、核苷酸等),而這篇文獻發現的新的促癌機制及靶點則是脂質代謝。事實上,脂質可以說幾乎參與所有生理過程與疾病。因為,脂質是生物膜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生物膜構成了細胞的各個亞細胞;同時,生物膜上還存在著大量的功能分子,例如該研究發現:SOAT1蛋白表達與細胞的膽固醇的攝入密切相關,進而通過影響分子整合素家族的豐度,參與腫瘤細胞的增殖和遷移。所以,脂質的變化可通過影響亞細胞、以及細胞膜上受體等大分子的功能,參與絕大部分的生理和病理過程。另外,脂質還是重要的能量物質。而脂質與腫瘤發生發展與治療的關系,目前的研究還非常少。換句話說,也許我們可以從脂質組作為起點,通過描繪脂質的異常變化,從另外一個路線找到調控脂質的關鍵蛋白SOAT1。
總結:
該研究不僅讓我們看到了早期肝癌的診斷、治療的新希望,也看到了蛋白質組技術應用于精準醫療的重要價值和應用潛力,同時我們還看到腫瘤代謝(尤其是脂質代謝)的重要性及其研究前景。該研究必將成為蛋白質組與精準醫療發展歷史進程中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向走在精準醫療前沿的我國研究者致敬!!
蛋白|修飾|代謝|脂質|結構確證
www.aptbiotech.com
T: 021-54665263
E: info_apt@sibs.ac.cn
Q: 1875681852